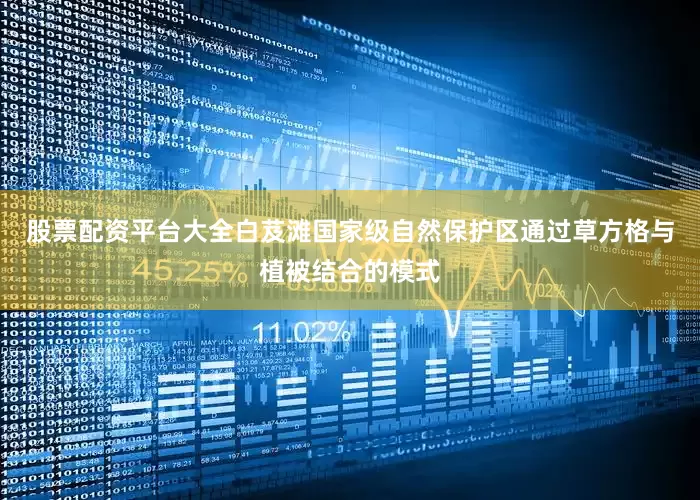荼靡辞春宴,谷雨启夏章。
今日谷雨,农历三月廿三。上午正忙着,突然“滴——”的一声,有短信通知来了。随手拿起手机,原来有人申请加微,是来自城区一位朋友的推荐。看看对方,竟是同门一族,想来该是比较熟悉的人吧,虽然,除了工作,我很少加微。通过后,很快,对方发来一个握手,并且自报家门,说是王留子村的,一声“哥”瞬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不知怎的,我的心“咯噔”一下,就这样,许多往事涌上心头。犹如毛衣上的一个线头,轻轻一拽,那些纵横交错、左右勾连的编织瞬间便散了开来……
屈指算来,我已经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。这其中,每次回家看望父母,也是来去匆匆,两点一线,绝不旁逸斜出。偶尔走在街上,看见那些年长者,问候一声,他们总要琢磨半天我是谁家的,也有眼尖的,直接呼出我的乳名;同龄的玩伴也已长大成人、星散四方,不是有事很难相遇;那些年少的于我更是形同陌路,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”,那一刻,诗人贺知章的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的感慨如急雨骤临,直浸心灵,风雨几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成家之后,自己的事情也多了起来,回家更是寥寥可数,除了逢年过节,很多时候,打个电话问问父母,聊聊家事,说说孩子,道道工作,仅此而已。
展开剩余71%王留子村和我们村直线距离应当不超过6公里,它和庄留子村东西毗邻,南面是单留子村。单留子村南有一大片果园,方圆近百米,是当时村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。再往南就是赣榆的母亲河——青口河,河的南岸便是朱村店的后店子村了,也因此,那条河在当地有了一个专名,叫做“后河”。
每年夏天,河堆上杂树丛生,枝叶繁茂,五颜六色的野花遍布其上,虫喃鸟鸣,蜂飞蝶舞,一派盎然。岸边的芦苇,成片成片的,秆茎昂然挺拔,叶片翠绿明艳。清澈的河水蜿蜒向东,缓缓流过。傍晚时,大人们不约而同,便会带着孩子来河里洗澡。下水前,再三告诫只准在岸边浅水处,中间河深水急,有危险,不许过去。下水后,大人们自觉离岸边远一点,在里面形成“人墙”,他们边洗澡边聊天,但眼睛无时不在“监视”着自家的孩子。那些孩子,似乎很乖,也很知足。一时间,这有限的区域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,水中嬉闹,岸上追逐,好不热闹。也不知是大人们安防做的好,还是河底清浅,我的印象中从未有溺水事情发生。后来,我终于得知了河的实际深度。有一次晚间洗澡时,有胆大的越过河中央,才知道水深处也不过齐腰已。
从地理位置上看,王留子村等和我们属于前村后庄的那种,“君居河之北,我栖河之南。近岸声可闻,遥波影难攀”。正是这条河,拉开了附近几个村子的距离,俗话说“隔河千里远”,这就给村庄间的交流往来带来很大的不便。那时交通还很不发达,平时,要去河北,如果有什么大事,必须向西行五六里,再从杨村西边的黄沙路经过青墩庙一直向北,经过一座大桥,便可进入北部。那里,是土城乡(现为塔山镇)的辖区。但,那似乎是一条“官路”,绕路不说,也不习惯,所以很少涉足。而多用常行的是另一条“民道”,连通两岸的还有西边邵庄村后的一架渡槽。附近的村民却偏爱这条悬空的捷径,仿佛踩着时代的脊梁穿行。
据说,渡槽建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,高约十五六米,宽约五米,长约八十米。渡槽是当时乃至现在乡镇间“南水北调”的重要水道,它像一条腾飞的巨龙,横跨在那条母亲河上。渡槽东面墙上镌刻着伟人毛泽东主席的诗句: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,毛体红字,耀眼夺目,笔走龙蛇,气势磅礴。这也正是那个时代人们改天换地、斗志昂扬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紧挨着渡槽东边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小道,路面用混凝土铺就,不是很平整,略有些粗糙凸凹,右边是稀疏的栏杆。由于凌河悬空,行走在上面总有些心惊胆战,而一些附近常走的人则安然若素,疾步如飞。更有奇绝者,骑车从50多度的斜坡上直冲下来,飘然而过引得路人侧目。但,更多的人偶尔路过,下车推行,不敢高声说笑,匆忙悄然而过。
时光飞逝,斗转星移。回家和父母说起村后的那条河,得知河堆早已不复存在,河道已被采沙船啃噬得面目全非,河里深不可测,浑浊的河水无声地向东流去,像哀怨,也似在倾诉。唯有那座渡槽仍矗立在夕阳里,槽身的裂缝里爬满青藤,像老人手背上的血管。我忽然想起母亲说过,渡槽建成那年夏天,附近几个村的许多男女老少都去河滩上观看,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让每个人脸上写满了自豪,新浇的混凝土在烈日下泛着水光,比现在的月亮还亮。
谷雨三候,萍始生。那些浮萍般的记忆,冷不防的,总会在某个寻常时刻突然冒出水面……
作者简介:王永济,男,网名又见炊烟,江苏赣榆人。从事教育工作,连云港市作协会员。喜音乐,好文学,作品散见于《赣榆报》、《赣榆文艺》、《连云港日报》、莱山文学、文化佳园、芳华旧梦、新浪新闻、中国作家网等平台、微博公众号。
发布于:北京市配资投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